2025年6月5日,兰德公司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办的关于中国对美供应链影响的听证会上做证词,分析美国防供应链所面临的中国产品和制造的挑战与风险,及美相关举措的成效和制约。主要内容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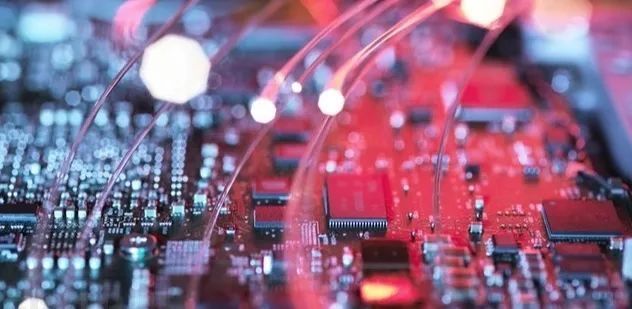
二、美国国防部及工业界应对供应链风险的措施
证词中提出美国国防部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识别和缓解供应链风险,但成效受到一定限制:
一是加强风险识别与库存储备,国防部DARPA启动了跨部门的供应链脆弱性评估项目,但是国防部缺乏对供应链全链条的透明监控;国防后勤局实施了大量战略物资储备,但还受限于对未来战时需求规模和品类的准确预测能力。二是推进技术替代与简化供应链,国防部正在推动开发不依赖广泛、复杂供应链的装备和能力,如国防创新小组(DIU)资助开发以供应链简单、供应源易从美商业部门获取为特征的项目,但这类项目可能牺牲技术先进性;美在推进“友岸外包”,试图将供应链转移至日、韩等盟国,但成本较高且仍无法完全摆脱中国的中间品。三是加大需求侧激励,扩大长期采购承诺,通过预付款或最低订单量鼓励本土产能建设。
当前美国各政府部门纷纷设置供应链中心以解决供应链风险,但同时带来更多政策协调问题。国防部更加重视按照军事所需建设供应链,与民口政府部门需求差异较大。美国家安全委员会曾试图统筹管理各部门的供应链政策,但目前委员会面临重组;国防部曾在应对工业基础和国家资源问题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但随着供应链问题存在于更广泛的经济中,部门统筹协调问题更加突出。
三、美国防供应链在应战场景下的突出风险
证词中指出,美国防工业具备应对稳定需求和明确短期市场波动的能力。但是,除了海军核动力、核武器开发和某些先进传感器等领域因为需求明确、资金明确,其相关供应链是相对安全的,总体上,美国国防工业基础没有很好应对供应链冲击、应对战时需求激增的能力,而且工业界也没有相应的内生动力。
证词中称,这不是中国的原因,中国为整个美国经济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的工业供给,而并没有证据显示其要削弱美国防工业基础。通常情况是,由于美政府将效率作为第一要求,美军工企业必须在完成合同过程中寻求最低成本的投入。在正常市场中,供应商做调整以满足需求,当需求激增时,是市场最终调整来满足激增需求。国防部试图通过使用投资基金模式,将有效的市场原则应用于订购和交付备件。这在稳定形势下是相对有效的。然而在需求超过正常和平时期的战争时期,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历史上美国依赖“民用转军用”弥补战时能力需求,应对供应链冲击,但这种方法依赖于一个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工业经济,具有可转换为国防生产的显著过剩能力,而那个时代已经过去。
四、几点认识
一是美国正转向“低成本冗余”供应链模式。证词提及乌克兰战场上大量使用廉价无人机消耗俄军的经验,认为可能影响美军未来装备发展,推动去高端化趋势。我国需关注美国在人工智能、无人装备等领域的低技术、规模化创新,防范其以量补质。
二是供应链安全议题成为对华遏制重要抓手。美国国会可能以“国家安全”为由扩大制裁范围,通过“小院高墙”等策略推进对华供应链脱钩,并联合盟友实施“次级”对华制裁和脱钩。但美国防供应链对华依赖是根植于全球分工体系的,短期难以替代。我国需利用好美对华依赖的薄弱点加强外交砝码,警惕美利用盟友推进去中国化的举措,并加快关键领域自主可控。
(科荟智库:穆果)




